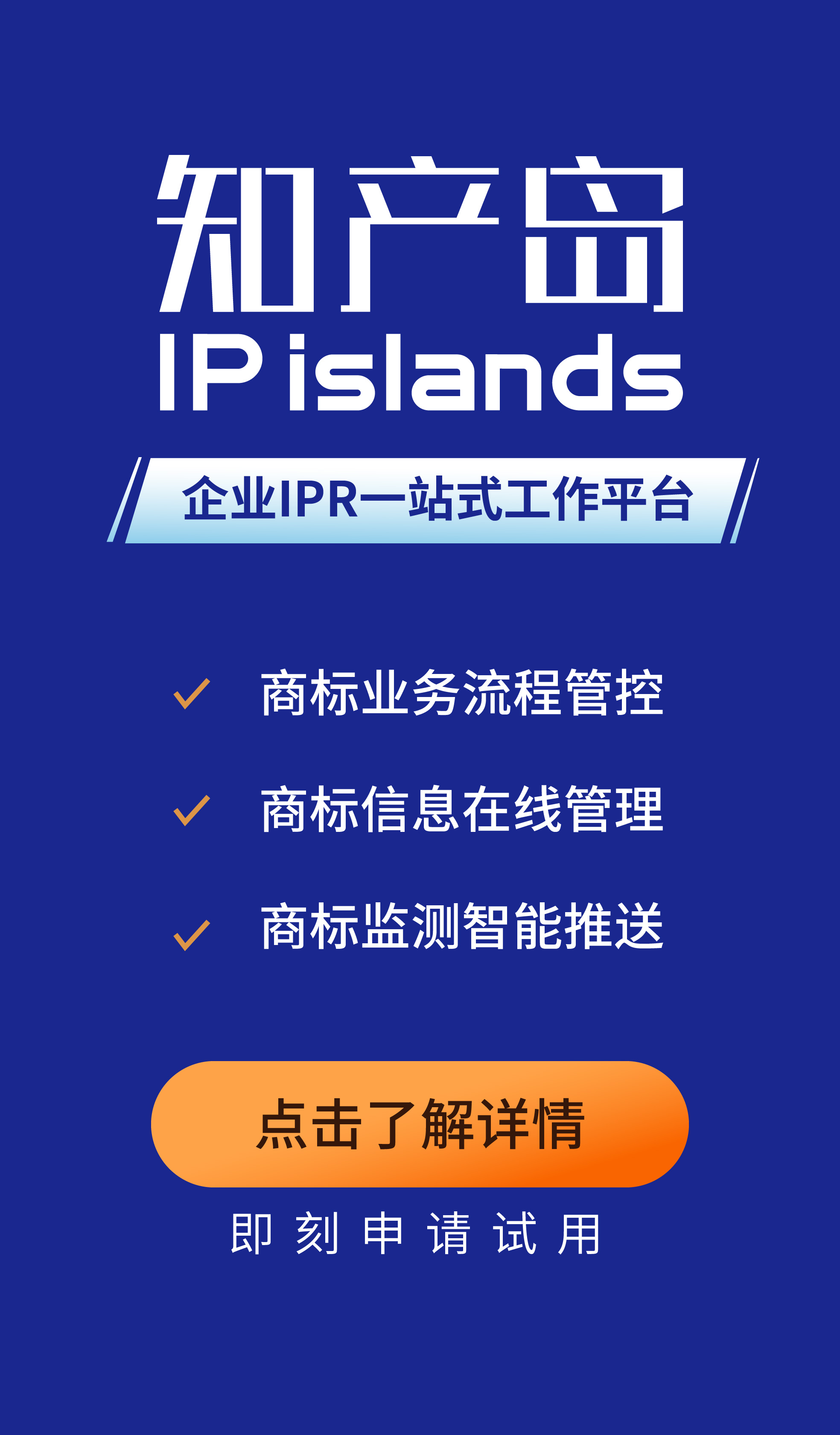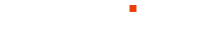#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IPRdaily立场,未经作者许可,禁止转载#
“本文尝试针对‘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规则提出一些探讨性意见。”
来源: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
作者:崔哲勇 刘涛 魏玮 孙理然
前言
通常认为,可预见性规则是一项起源于美国司法实践的专利侵权抗辩规则,用于限制等同原则的适用范围。可预见性规则在国内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03年10月最高院的《关于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会议讨论稿 20031027-29)》,该讨论稿的第十一条第三款为“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的变换特征对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在专利申请日是显而易见的,而申请人未将该变换特征写入权利要求,权利人在侵权诉讼中主张对该变换特征适用等同原则认定为等同特征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北京高院在其2017年修订的《专利侵权判定指南》的第60条中,新增了“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方法:“60、对于发明权利要求中的非发明点技术特征、修改形成的技术特征或者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如果专利权人在专利申请或修改时明知或足以预见到存在替代性技术特征而未将其纳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在侵权判定中,权利人以构成等同特征为由主张将该替代性技术方案纳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的,不予支持。”
虽然最高院在二十多年前就对“可预见性规则”进行了讨论,然而直至二十多年后的今日,“可预见性规则”仍然没有被写入司法解释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规则的实施难度之高、争议之大。
但近年来,“可预见性规则”在国内的司法实践中却经常被适用,通过对知产宝收录的2019-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做出的判决书进行统计发现,2019-2024年分别有2件、5件、2件、3件、7件、2件案件涉及“可预见性规则”。在没有司法解释等成文法进行规制的情况下,“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必然面临着标准不统一、争议多的问题。前述统计的2020年的5件二审判决均撤销了一审判决;2022年的3件二审判决中,有2件撤销了一审判决。这从侧面说明“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标准存在争议。“可预见性规则”到底应当不应当适用、究竟如何来正确适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尝试针对“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规则提出一些探讨性意见。
PART 1
针对可预见性规则是否应当适用的争议
北京高院的《专利侵权判定指南》支持适用可预见性规则限制等同侵权,其核心理由是强化权利要求的公示作用,避免专利权人不适当地扩张专利权保护范围,压缩创新空间和损害公共利益,特别提出倒逼权利要求撰写质量提高等考量。现实中也有不少案例支持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
但学术界主流的观点却有很多是否定“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认为该规则对于专利权人的要求过于苛刻,可能会导致等同侵权的消亡,从而损坏专利制度保护专利权人、鼓励创新的宗旨。
现最高法民三庭综合办公室主任、二级高级法官助理马云鹏认为:
申请日没有发生非实质性变化的替代性技术特征也不应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等同之外,至少不能因为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而被纳入“可预见性”的范围,给予其无需进行等同侵权比对的豁免,这样会极大地压缩等同适用的空间,损害专利权人的利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权利要求中的每一处表述或每一个措辞,都是经过精心编织且具有划定保护范围“藩篱”作用的,如果类似可预见性规则这种特意排除类的规则被随意适用,则会产生一种以偏概全的思路倾向,即未在权利要求书中“登记造册”的技术方案都被默认为是保护范围之外的,无法被认定为等同。[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鹏认为:
如果仅以救济专利权人因技术发展的不可预测性而导致的利益受损作为等同侵权的法理基础,那么中日两国的实践中,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案件是因技术发展在申请日后出现了新的可置换部分而导致的适用等同侵权。在此种法理基础上理解等同侵权,导致的可能不是等同侵权适用的复兴,而是等同侵权适用的消亡。……更为重要的是,该理论并不救济专利权人因先申请主义导致的专利申请文件的纰漏,而一律要求专利权人将申请日可以预见的可替换技术方案全部写入权利要求。这种要求权利人撰写一份“完美的权利要求”的做法,并不会增进整体的福利。[2]
郑州大学张迩瀚认为:
该规则对于申请时等同原则的适用空间所产生的限制性影响则几乎是致命的。在申请时可以预见的等同物不得适用等同原则,而能够适用等同原则的是不可预见的等同物。……这也就意味着在可预见性规则之下的申请时等同原则的适用空间名存实亡,不具有任何生命力。[3]
另外,还有观点认为,由于专利授权程序中的修改规则过于机械严苛,适用可预见性规则对于专利权人将是不公平的。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在2013年发布的《等同侵权的司法认定》”一文。
通过以上观点的罗列可以看到,可预见性规则作为等同原则的排除适用规则,极大地限缩了等同原则的适用空间,二者之间的冲突使得学术界担心等同原则的适用被架空。在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北京高院的可预见性规则和众多司法判决都提出,专利权人在“明知”和“足以预见”替代性特征时,就要面对等同原则不能适用的后果。这种仅仅从替代性特征是否可预见来决定是否排除等同原则的适用是否过于严苛?
二是专利权人在申请日之前是否明知、是否能够预见,是专利权人在申请日之前一种主观思维状态,这是一种难以证明的事实,引入这样的标准是否能在实践中保证其准确的适用。
笔者认为,无论是出于保障社会公众的合法权利不被侵害,还是倒逼专利撰写质量的提升,学术界并不排斥对等同原则的适用进行合理的限制。历次司法解释提出的捐献原则、特意排除原则、符合发明目的原则等等,均是对专利权适用等同原则的限制,但都得到业界的拥护。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厘清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条件和判断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为权利人和社会公众划分出合理可预期的边界,实现其法律价值。
PART 2
可预见性规则在各国的司法实践
(一)美国
1、Johnson & Johnston案:可预见性规则的诞生
2002年3月,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Johnson & Johnston案作出判决。本案原告(专利权人)主张构成等同的方案是记载在专利说明书中,但没有写入权利要求的方案。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本案的13位法官中,有12位法官认为根据捐献原则,原告不能主张等同;Radar法官也是其中一员。
但Radar法官在其并列意见中(concur)提出了补充了另一种理由:为了平衡权利要求的公示作用、等同原则保护权利人的作用,等同原则不能覆盖专利撰写者在申请过程中可以预见并写入权利要求的内容。一般认为,Radar法官在该案并列意见中的观点对我国“可预见性规则”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2、Ring & Pinion案:对可预见性规则的否定
2014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Ring & Pinion案中明确否定了Radar法官在Johnson & Johnston案提出的“可预见性规则”,其指出:可预见性对等同原则适用的限制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可替换性有利于在等同原则下认定侵权,是长久以来十分清晰的规则。
3、UCB, Inc. v. Watson Laboratories Inc.案:再议可预见性规则
在2019年的UCB, Inc. v. Watson Laboratories Inc.案(优时比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又指出:Ring & Pinion案认定可预见性本身(“per se”)不能禁止等同原则适用,但亦不排除等同方案的可预见性作为一个因素,在有些情况下对反对等同侵权的主张有支持作用。而在可预见性的具体判断上,该院在本案中引用2012年箭牌案(Wm. Wrigley Jr. Co.)[4]考虑的因素,认定原告的等同主张成立:(1)专利公开的内容是否强调了等同方案不具备的优点;(2)权利要求的相关特征是否存在对说明书内容的捐献(即如果权利要求连说明书中的方案都不寻求全部保护,则倾向不再适用等同原则扩张其保护范围);(3)发明人是否知道等同方案。
从箭牌案和优时比案中可以看出,判断“可预见性”考虑的三个因素中,前两个因素其实与“特意排除/发明目的排除原则”和“捐献原则”(或捐献原则的类推)类似,且都基于专利内部证据进行考察。即便第三个因素允许引入外部证据,亦限于与发明人直接相关的证据,且须证明发明人知道被控等同的内容可以适用于专利方案中(而不仅是笼统地了解被控等同内容)。例如优时比案中,发明人甚至曾在申请日前的可行性报告中,将被控等同成分作为常用成分之一列举;但其没有进一步测试该成分,也没有将该成分写入权利要求。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即便如此也不能认为发明人放弃了就被控成分主张等同。
(二)日本
日本最高法院在“马沙骨化醇案”中就此问题指出:“在专利申请时,对与权利要求记载的特征相异的部分,尽管专利申请人容易想到该特征,但是并不仅仅因为未将其写进权利要求中就认为第三人应该产生将该特征排除出专利保护范围之外的信赖。如果仅因为专利申请人在申请时可以容易想到某一特征但却没有写进权利要求就一律排除等同原则的适用,那么在先申请原则的尽快申请压力下就会强加给专利申请人将预想到将来可能存在的各种侵权样态写入权利要求的义务,而对通过说明书了解到技术方案的第三人来说,可以不受时间上的制约发现与权利要求相异的技术特征进行替换,从而轻易地规避侵权的惩罚,应该说这样的法律适用并不恰当。”依据该判旨,申请时的已知替换,并不妨碍等同侵权判断要件的适用。[5]
(三)中国
以“可预见”作为关键词,本文选取了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涉及6件判决,对这些判决中所体现的“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标准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1、(2015)民申字第740号
最高院在本案中认为被诉侵权产品“一体式盖母上表面呈平面”与涉案专利“进水套上表面呈锥面”的特征不构成等同的原因在于,“要锥面或平面均是涉案专利申请时,该领域技术人员普遍知晓的技术方案,因此,专利权人将权利要求中该技术特征限定为锥面是将平面排除在涉案专利保护范围之外。鉴此,在侵权判定时,不能将技术特征‘锥面’扩张到‘平面’予以保护,否则将有损社会公众对专利权保护范围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信赖,从而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
该案被很多人解读为最高院适用“可预见性规则”的第一案,但其含义显然与北京高院的可预见性规则有所区别——本案进行“预见”的主体是代表社会公众的本领域技术人员,而不是专利权人。进一步分析本案案情,可以发现涉案实用新型专利的实施例明确“进水套的锥面与浮球为线接触,所以不会产生腐蚀……避免了跑水事故的发生”。由此可知,申请人在申请时明确了“进水套上表面呈锥面”的特征解决了相应的技术问题,实现了相应的技术效果。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阅读了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之后,可以发现专利权人在专利文件中特意强调“锥面”的技术效果,又未将“平面”写入保护范围,也就可以预见专利的保护范围不会延伸至“平面”方案。这似乎落入了“特意排除原则”的适用范围。
2、(2020)最高法知民终1429号
本案涉案专利在申请中修改增加了多个技术特征,其中包括设置霍尔传感器以及基于霍尔传感器信号查找正弦表以获取角度信息等。专利权人主张被诉侵权产品使用红外对管替代了霍尔传感器、使用CORDIC通用算法替代了查找正弦表,但功能和效果与涉案专利一致,构成等同。
最高院在本案中的观点与(2015)民申字第740号类似,其中“预见”的对象也是“社会公众对专利保护范围”的预见,判决中认为:红外对管为涉案专利申请时该领域技术人员普遍知晓的技术手段。专利权人将权利要求中的该技术特征限定为霍尔传感器,就是将其他传感器排除在其保护范围之外,在进行侵权判定时,不能将“霍尔传感器”扩张到红外对管等其他传感器予以保护。“否则有损社会公众对专利保护范围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信赖,损害社会公众利益”。
应当注意,本案区别技术特征并非仅仅是“霍尔传感器”和“红外对管”,还包括由此进一步衍生出的后续处理的诸多不同。最高院在判决结论部分明确确认,被诉侵权产品的红外对管方案与权利要求中的霍尔传感器方案在角度检测、函数算法上均为不同的技术手段,二者不构成等同特征。也就是说,本案是在专利权人不能证明被诉侵权方案与涉案专利满足“三基本”的情况下判令专利权人承担不利后果,并非仅因为“可预见”就判决专利权人败诉,更不是适用北京高院的可预见性规则而如此判决。
3、(2021)最高法知民终192号
本案为最高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2021)第22号。涉案专利发明名称为“电动绿篱机”,权利要求明确限定了“电动绿篱机”,而被诉侵权产品采用燃油发动机为动力源驱动。
最高院认为,燃油驱动方案与电驱动方案不构成等同,并明确“从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基于对环保效果的追求,专利申请人并不寻求保护以燃油发动机作为动力源的绿篱机技术方案……在此情况下,若在判断被诉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时,将燃油发动机驱动与电机驱动认定构成技术特征等同,则不利于专利权利要求公示作用的发挥和社会公众信赖利益的保护。”在本案的裁判要旨中,最高院指出:专利权利人在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未将其明确知晓的技术方案写入权利要求,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后认为专利权利人明确不寻求保护该未写入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的,一般不应再通过等同侵权将该技术方案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
本案判决内容和裁判要旨中,虽然与北京高院的可预见性规则类似,也提及“未将其明确知晓的技术方案写入权利要求”,即考察了专利权人在申请或者修改时的认知状态,但采用的标准为专利权人“明确知晓”而不是“足以预见”。更为重要的是,本案中排除等同原则的适用还需要满足“从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专利申请人并不寻求保护……”这样的表述,或者说“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后认为专利权利人明确不寻求保护该未写入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本案裁判要旨)。这实际上更接近“特意排除原则”。
4、(2024)最高法知民申464号
本案的一个争议焦点在于:权利要求中的推力轴承和被控侵权方案中的深沟球轴承是否构成等同技术特征。被告主张,专利权人在撰写涉案专利申请文件时,并未将申请日前的公知技术(深沟球轴承)纳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故根据(2021)最高法知民终1924号指导案例[6],本案不应再适用等同原则将该技术特征纳入保护范围。
最高院在再审中认为,判断深沟球轴承与推力轴承是否构成等同技术特征的关键在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后,是否认为专利权人特意强调推力轴承,并排除深沟球轴承。如果专利权人在权利要求中特意强调某一特征的用语含义而有意排除特定技术方案的,不应再通过适用等同原则将被排除的技术方案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具体到本案中,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阅读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后并不能得出上述结论,因此,本案可以适用等同原则。
尽管被告曾根据(2021)最高法知民终1924号主张“可预见性规则”,但最高院经再审,厘清了“可预见性规则”的实质。该案的裁判思路与192号案件相同:站在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角度对说明书和审查及无效档案进行技术解读,判断专利申请人是否有不寻求保护被诉侵权方案的意思。
5、(2019)最高法民申3188号
本案中,权利要求中包括特征“高低相间排列的弹性支撑片”,而被诉侵权产品中弹性支撑片等高排列。就专利权人的等同侵权主张,最高院认为:根据涉案专利权利要求、说明书附图,“弹性支撑片高低相间应当理解为支撑片的高度不同……相间排列”,且 “涉案专利申请人在专利申请时足以预见到存在等高排列的替代性特征,但未将其写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故弹性支撑片等高排列的技术特征不应当被认定为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弹性支撑片高低相间排列’等同的技术特征”。
本案中,最高院审查是否“足以预见”时,其判断标准是专利权人是否足以预见,似乎与北京高院的可预见性规则观点类似。但仔细分析可知,本案最高院裁判思路的本质仍然是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角度出发,通过阅读说明书(而不是任意的外部证据),从而解读权利要求所限定的“高低相间排列”的技术含义,将明显不符合技术人员理解的“等高排列”排除出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最高院实质上认为专利权人在权利要求中撰写“高低相间排列”的特征,就是在多种排列方式中选择了特定的一种方式,这与“特意排除原则”十分类似。
6、(2022)最高法知民终2844号
本案中,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限定存在照明光源和探测光源,且是以一字型激光源作为探测光源;而被诉侵权产品则设置了LED光源和特殊形状透光孔作为探测光源。最高院经分析认定不构成等同侵权。
就“可预见”问题,最高院认为:专利权人亦认可在涉案专利申请日前,LED光源通过遮挡也能够达到激光源的效果,但在撰写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书时仍将LED光源和激光源进行了明确区分。即专利权人在涉案专利申请时明知或足以预见到存在替代性技术特征而未将其纳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除了可预见问题之外,最高院在本案中亦给出了其他判决理由: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涉案专利说明书,可知涉案专利在申请时已经对LED光源和激光源进行了区分,明确了采用一字型激光源作为探测光源具有有益技术效果。涉案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之中,专利权人亦强调了涉案专利以某种激光源作为探测光源。而这些理由显然更接近特意排除原则。
PART 3
可预见性规则适用的探讨
从对可预见性规则的历史渊源及域外实践可以看出,可预见性规则从提出以来,即面临着质疑,并未如捐献原则一样,形成一条法定的或者公认的规则。类似地,在我国,除地方性司法文件以外,法律、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界定。最高院的司法文书虽有类似表述,但也均未曾明确提出过可预见性规则,反映出最高司法机关对于可预见性规则的审慎态度。从相关裁判文书反应的内容来看,最高院在专利侵权判断中始终强调要平衡专利权人与公众利益、促进专利撰写质量的立场。因此,以“可预见性”作为考量因素,与捐献及特意排除互补适用,从而全方位的限制等同侵权的扩张适用,应该是其追求的目标。
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由于“可预见性”在实践中判断上的主观不确定性,与捐献、特意排除、符合发明目的等规则的适用场景及职能重叠,容易造成实践中的困惑。特别是在适用与否、如何适用上有着极大的争议和不确定性。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可预见性规则的理解和适用应当基于权利要求的公示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第一,坚持权利要求的公示原则。
专利权是一种对世权,公示原则是其基本原则之一。专利制度的本质是以公开换取垄断,说明书的内容是公开的范围,权利要求的内容是垄断的范围。专利权一旦被授权公告后,社会公众会信赖权利要求的公示作用,相信其权利边界不会扩大,据此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由此形成信赖利益。在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实践中,为了防止滥用等同原则导致不合理地损害专利权利要求的公示性,进而损害社会公正的信赖利益,有必要适当限制等同原则的适用。
第二,坚持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确认民事主体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专利权在授权和确权乃至行权过程中,专利权人通过专利文件的撰写、修改、意见陈述等行为,明确的表达其真实意思,这些表达都将成为其划定专利权与社会公众之间权利边界的重要依据。专利局根据专利权人从上述各种形式体现的真实意思表达,正确理解并界定其发明创造的内容并审查其是否符合授权条件;社会公众通过专利权人的上述真实意思表达,合理预期其专利权要求保护的范围以及排除保护或捐献给公共领域的范围,从而自由的从事民事活动。因此,专利权范围的可预见应当是专利被授予和保护的前提条件,特别是,这样的可预见本质上应当是基于专利权人的意思自治来实现的。
因此,笔者认为可预期规则实质上并非是一种操作性的规则,换言之,可预期规则不同于捐献原则或者特意排除原则这样的操作性规则。可预期规则实质上是指导建立捐献原则或者特意排除原则的法理上的、上位的规则。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案例,我们会认为可预见性规则与捐献原则、特意排除原则存在着竞合。
(二)可预见性规则的具体适用
1、“可预见性规则”中“预见的主体”是社会公众,而非“专利权人”
首先,基于专利的公示原则,撰写权利要求的目的是向社会公众公示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让社会公众会信赖权利要求的公示作用,由此形成信赖利益。也就是说,通过权利要求书来“预见”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主体是“社会公众”,而非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有义务通过专利文件让“社会公众”能够“预见”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社会公众”也应当通过专利文件“预见”到哪些技术是处于专利的藩篱之中,而哪些技术是被专利权人放弃保护或者捐献给公众。因此,“可预见性规则”的“预见”主体也应当是“社会公众”。
基于此,某些司法实践中考察证明“专利权人”在申请日时是否“能够预见”到可替代的技术特征,是缺乏合理性的。因为这与专利权的公示作用完全无关。
2、“可预见性规则”中“预见的对象”是专利权人寻求保护哪些范围以及排除或不寻求保护哪些范围,而非预见专利权人在申请日是否知晓未写入保护范围的等同替代方案
专利权的对世属性以及专利权人的意思自治,乃至专利权本身贡献与保护相匹配的原则,都决定了专利权应当明确向社会公众划定其保护范围,达到公众可预见的程度,从而达到专利权的公式作用。在此情况下,可预见性规则的预见的对象,当然应当是社会公众对于专利权保护范围的预见,而不能仅仅是某个技术特征是否属于申请日时可预见的替代技术特征的预见。唯有如此,才能维护社会公众和专利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3、“可预见性规则”中预见的依据,应当是专利文件的内部证据为主,遵循专利权人的意思自治
专利权人向社会公众划定其保护范围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专利文件的撰写以及意见陈述。通过这些书面的方式,专利权人阐明其发明创造、表达其技术贡献、寻求其技术保护。专利局和法院据此审查其是否应当授权以及确定其保护范围,社会公众据此明确其权利义务的边界。而这些专利文件的撰写和意见陈述都应当是明确的、符合专利权人的意思表示,并且禁止反悔。
未记载在专利文件和审查档案中的外部证据,仅仅针对个别词汇的解释存在价值,但针对专利权人寻求哪些范围的保护,放弃或者捐献哪些范围的保护这样主观的意思表示,外部证据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4、“可预见性规则”是捐献原则、特意排除原则、符合发明目的原则等的上位指导规则,是指导其使用的根本思路方法;而捐献原则等则是可预见性规则实践落地的具体表现形式
对于“捐献原则”而言,专利权人在说明书中已经明知并记载了特定方案,但通过不将该特定方案写入权利要求的行为,向社会公众表达了其放弃该特定方案保护的意愿。而社会公众根据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等内部证据所呈现的上述事实可以预见,专利权人不寻求保护该特定技术方案,因此可以适用“可预见性规则”的排除等同的适用。
对于“特定排除”“发明目的排除”原则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根据说明书这一内部证据,公众可以预见专利权人特别强调保护具有特定技术效果的技术方案,从而预见专利权人不寻求保护其他技术方案时,也可以适用“可预见性规则”排除等同的适用。
PART 4
结论
以上的观点仅仅代表笔者非常简单的思考,笔者认为,“可预见性规则”并不会导致等同原则消亡。相反,厘清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条件,使其发挥对等同原则合理的限制则是非常有益的。美国在可预见性规则的实践中多次提出抵触和混乱的观点,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但是反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判决,其实一直都秉承着以社会公众的视角,基于专利权人在专利文件中的真实意思表达,来判断专利的保护范围是否能够被合理预见的标准。这其实与笔者的观点是完全符合的。
注释:
[1]马云鹏.等同侵权判定中可预见性规则的理解与适用[J].中国应用法学,2023,(05):178-189.
[2]张鹏.等同侵权限制规则的适用研究——以中日比较为中心[J].知识产权,2023,(06):86-106.
[3]张迩瀚.我国专利侵权中可预见性规则司法适用问题研究[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9(02):37-41.
[4]箭牌案中并未明确提到“可预见”,但优时比案将箭牌案考虑的三个因素作为“可预见”的判断因素。
[5]张鹏.等同侵权限制规则的适用研究——以中日比较为中心[J].知识产权,2023,(06):86-106.
[6]关于(2021)最高法知民终1924号案,一个有趣的情况是:被告代理人虽然取得胜诉,但也撰文指出,该判决的裁判规则“对等同侵权限定程度过大,个人认为属于用力过猛,需要各方更深入的讨论。至少要对其适用要做更严格的规定。”(https://mp.weixin.qq.com/s/Xc3BE0sFZ-Va1LLVYxwOh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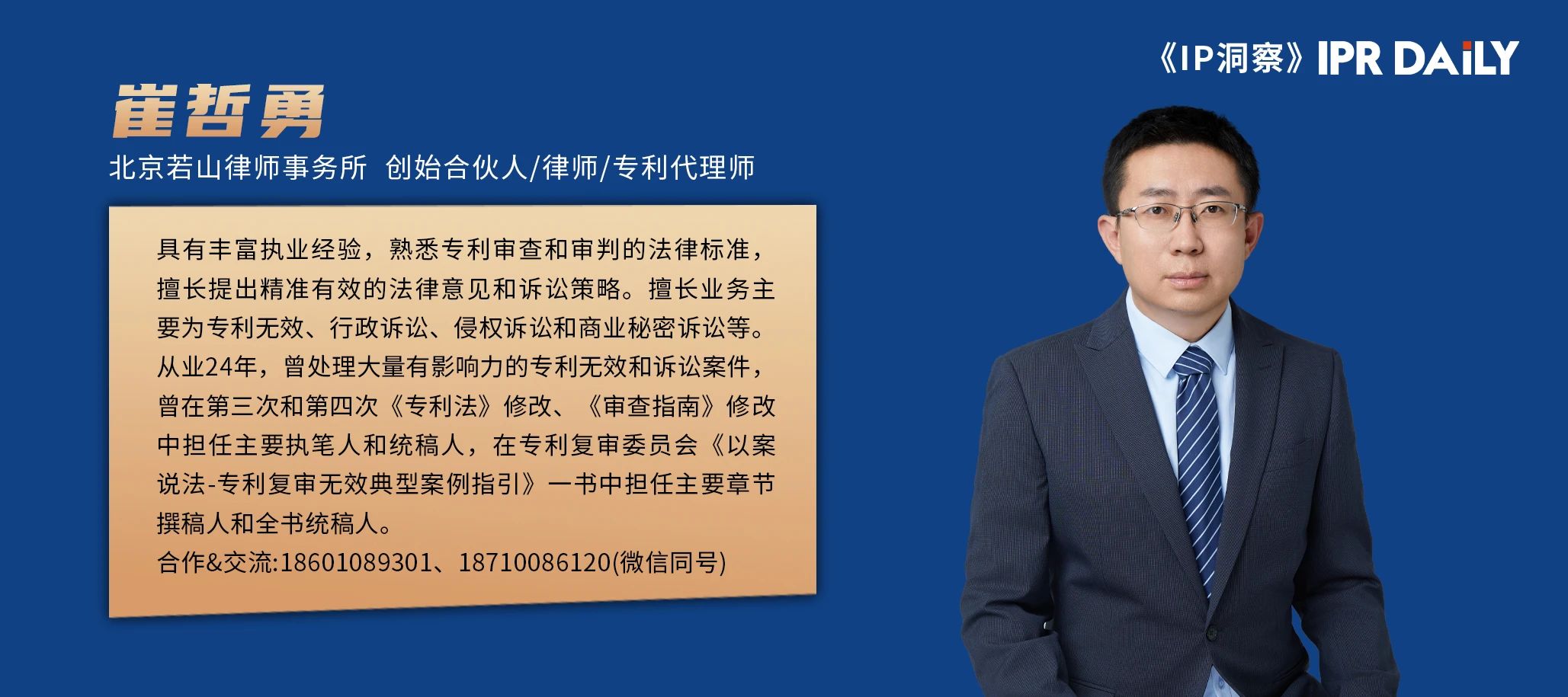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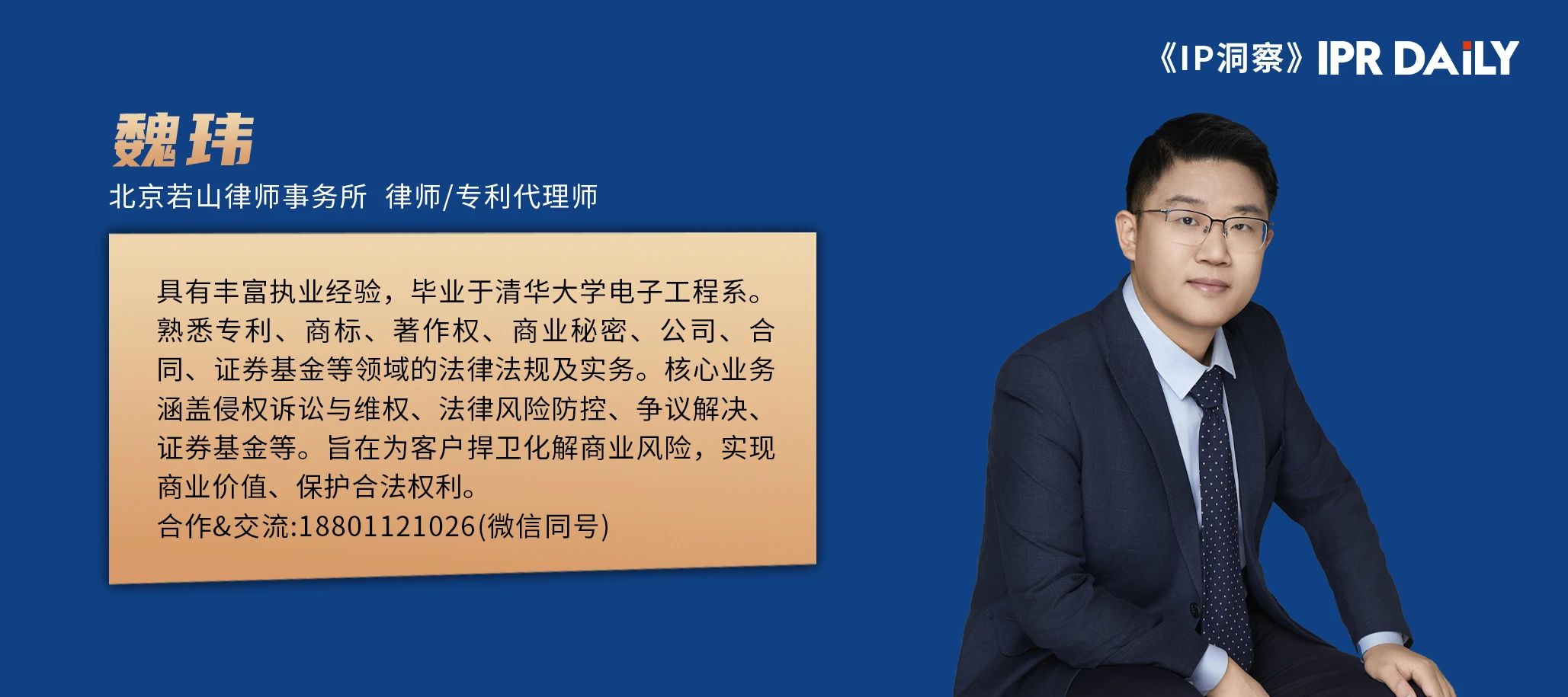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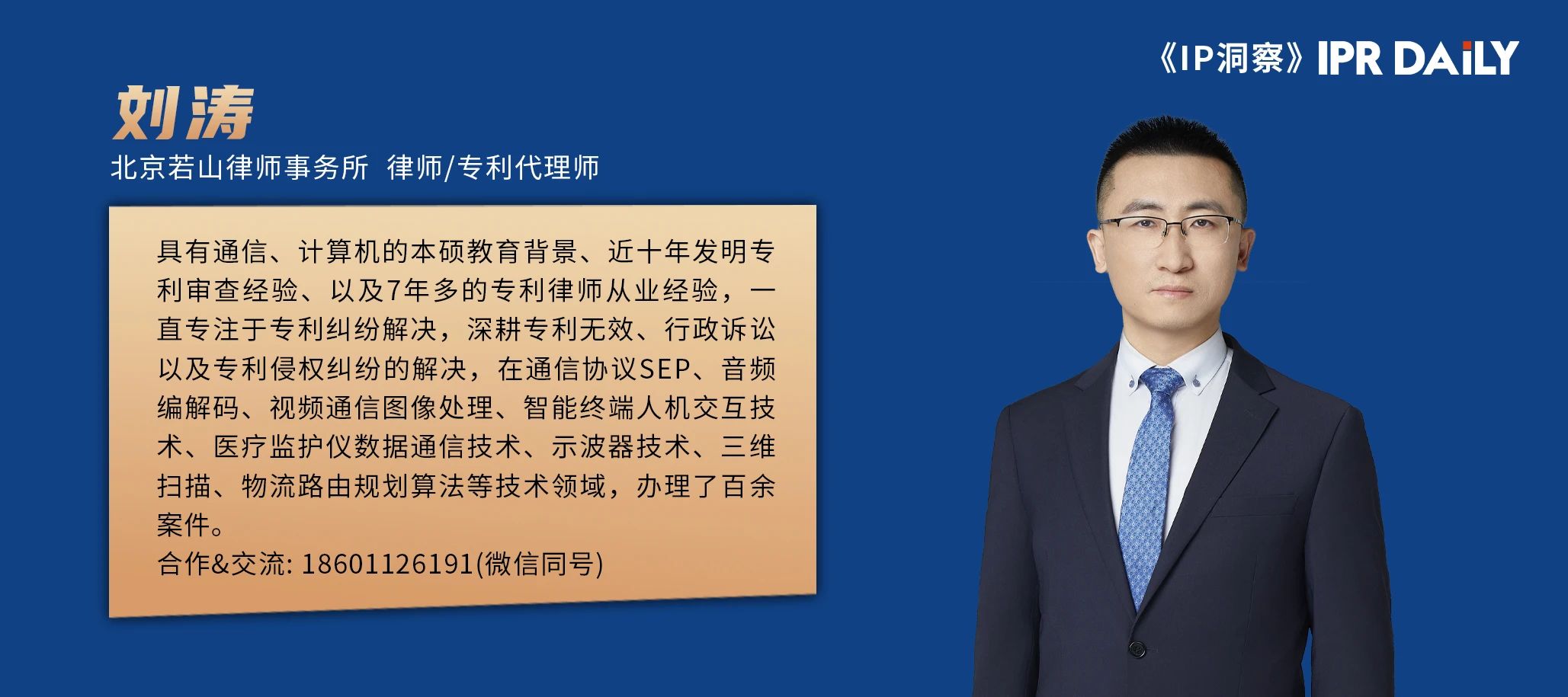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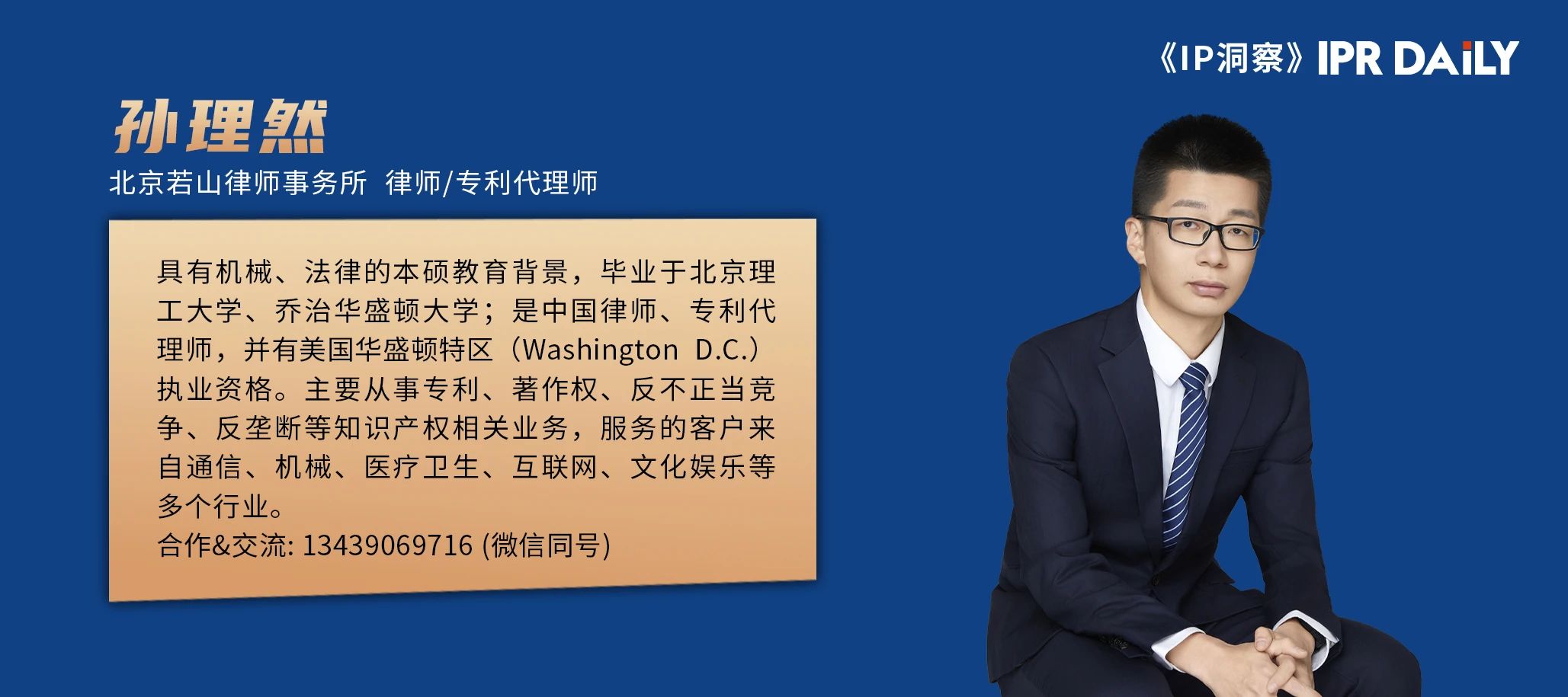
(原标题:可预见性规则的司法适用建议)
栏目支持,共建合作伙伴持续招募
来源: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
作者:崔哲勇 刘涛 魏玮 孙理然
编辑:IPRdaily辛夷 校对:IPRdaily纵横君
注:原文链接:可预见性规则的司法适用建议(点击标题查看原文)

「关于IPRdaily」
IPRdaily是全球领先的知识产权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致力于连接全球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人才。汇聚了来自于中国、美国、欧洲、俄罗斯、以色列、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科技公司及成长型科技企业的管理者及科技研发或知识产权负责人,还有来自政府、律师及代理事务所、研发或服务机构的全球近100万用户(国内70余万+海外近30万),2019年全年全网页面浏览量已经突破过亿次传播。
(英文官网:iprdaily.com 中文官网:iprdaily.cn)
本文来自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并经IPRdaily.cn中文网编辑。转载此文章须经权利人同意,并附上出处与作者信息。文章不代表IPRdaily.cn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iprdaily.cn”

 共发表文章
1206篇
共发表文章
1206篇- 我也说两句
- 还可以输入140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