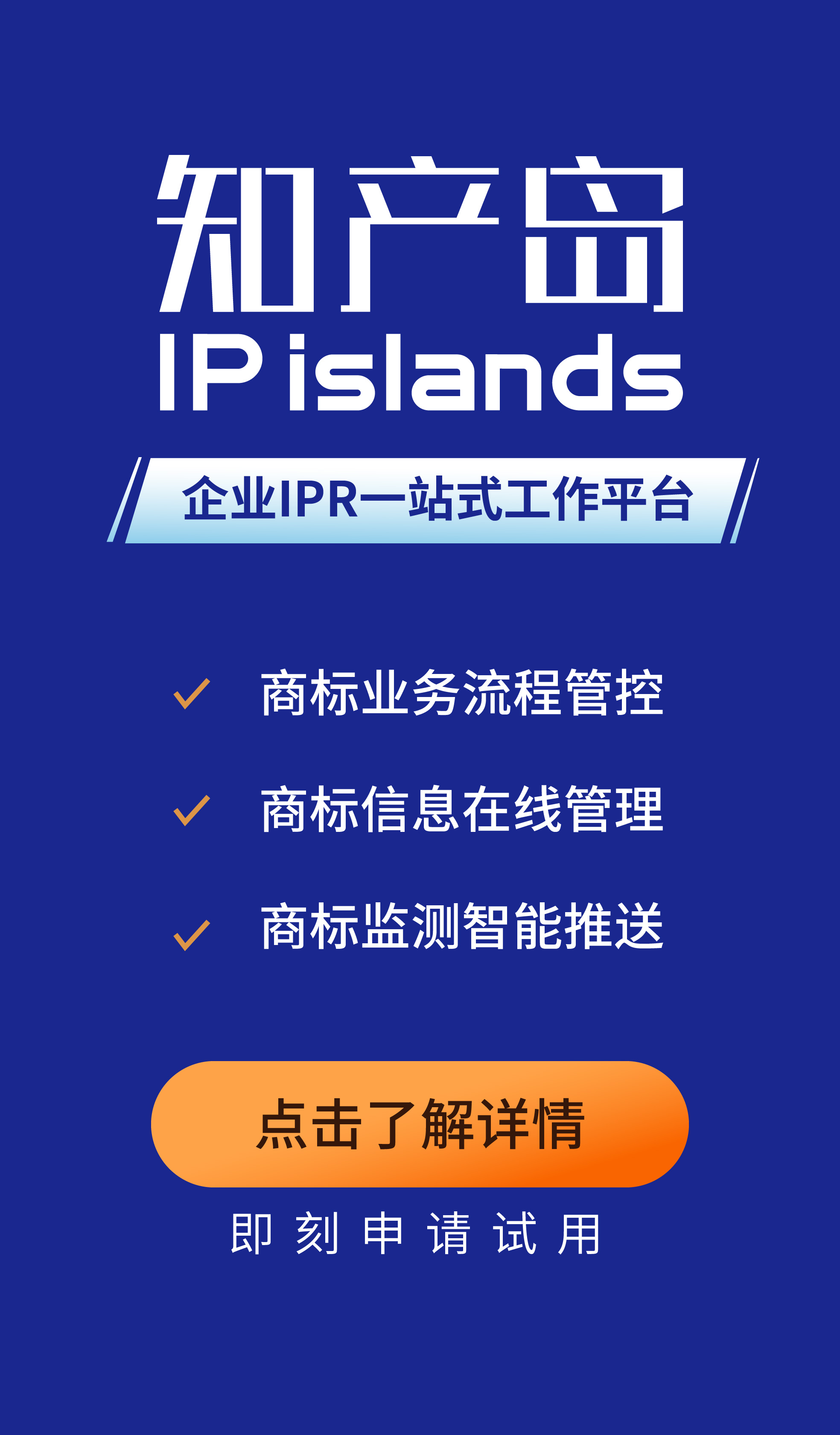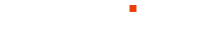#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IPRdaily立场,未经作者许可,禁止转载#
“本文以‘为发明投资’的逻辑框架为起点,通过建构知识产权流转的循环模型,剖析NPE在知识产权全链条中的作用,最终揭示其在保障知识产权流转的交易安全与降低知识产权流转的交易成本双重价值。”
来源: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
作者:张鹏 王博琳 郑书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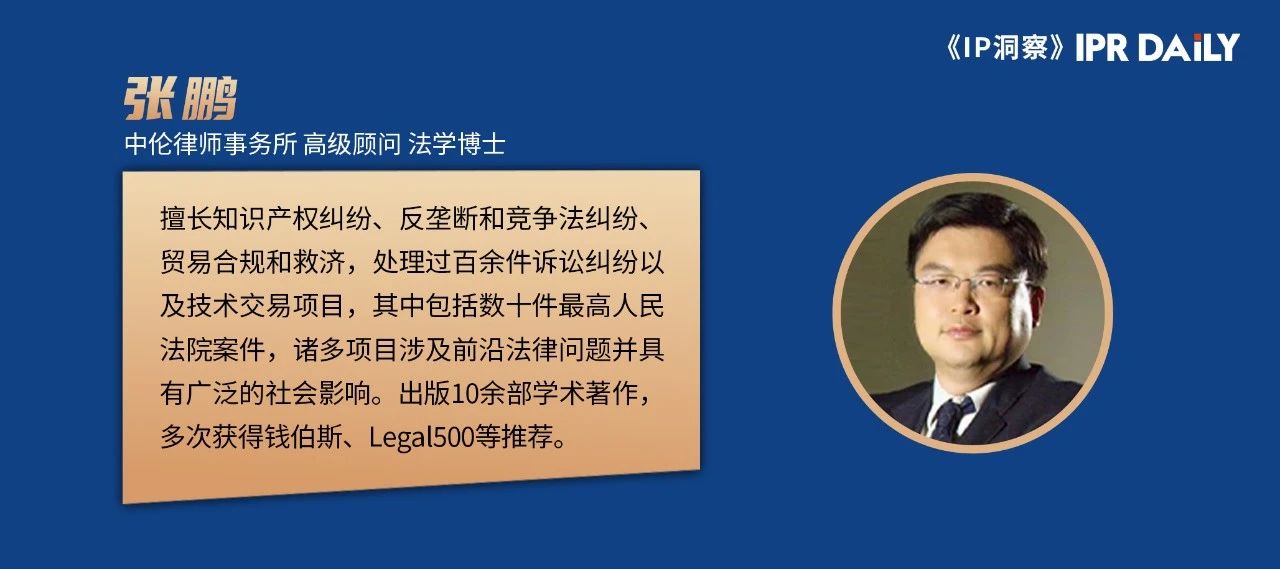
前言
促进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促进知识产权运营,最为根本的是保障知识产权流转的交易安全与降低知识产权流转的交易成本,通过知识产权经济调节解决不完全信息问题。专利非实施实体自诞生以来,始终处于法律与商业讨论的漩涡之中,同时通过对知识产权流转的深层影响,逐渐显露出不可替代的价值。纵观发明投资理论的演进轨迹,专利非实施实体的法律角色呈现出鲜明的辩证特征,既是传统知识产权制度的挑战者,又是现代创新经济的建构者;既是资本逐利性的物质载体,又是技术扩散的法治化通道。其通过市场机制填补法律制度的适应性缺口,在维护交易安全与降低交易成本的方面发挥其独特的积极作用,这种价值实现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经济指标提升,也可从技术保护的防御性工具转变为创新驱动的生产性资本。在数字技术重构全球产业格局的当下,深入理解专利非实施实体在发明投资理论中的体现、回归专利非实施实体的本质特征,有利于超越“遏制”或“放纵”的简单政策选择,真正释放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赋能潜力。
关键词:专利非实施实体 知识产权运营 交易安全 交易成本 发明投资理论
知识产权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核心生产要素,其流转效率与价值实现直接决定了创新生态的活力。《一文读懂NPE:含义如何、从何而来、如何理解?》一文分析了(英文全称为Non-Practicing Entity,简称为NPE)的基本含义,以及如何理解NPE的作用,认为NPE自出现以来,始终处于法律与商业讨论的漩涡之中,同时通过对知识产权流转的深层影响,逐渐显露出不可替代的价值。而本文以“为发明投资”的逻辑框架为起点,通过建构知识产权流转的循环模型,剖析NPE在知识产权全链条中的作用,最终揭示其在保障知识产权流转的交易安全与降低知识产权流转的交易成本双重价值。
一、发明投资理论的知识产权流动框架
第一,发明投资理论的总体背景:技术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关键力量,技术创新需要投资支持,发明投资理论应运而生。专利权的本质是法律对创新技术成果赋予的排他性权利,核心功能在于通过确定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进而激励创新并促进技术扩散。然而,这一制度设计自诞生之初便隐含着深刻的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专利权体现于不允许他人擅自使用专利,满足专利权人通过法定的“垄断权利”回收高昂的研发成本;另一方面,社会公共利益对技术成果也提出了要求,即尽可能使技术得以广泛传播,进而推动产业创新的整体进步。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关键力量,而技术创新尤其需要金融支持,特别是在技术周期缩短导致创新风险增加的情况下。[1]创新过程自身是不稳定且不确定的,然而此类不确定性与风险还是不同的,研发过程中人们既不清楚成功的概率,甚至不能准确预测创新结果的形式[2],主要来源于信息缺失或认知的局限,而风险性则侧重于能够识别潜在问题但无法完全规避的情况。
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例,1925年美国最早的自动驾驶汽车由Houdina无线电控制公司的创始人工程师Francis Houdina在纽约市的百老汇实现,被称为美国奇迹。1960年左右,受到美国科研风潮的影响,日本国立先进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开始研究自动驾驶,当时的人们思路依旧是在行驶路线上铺设感应电缆,通过有线链接的方式传输信号。时间到了2009年,谷歌启动“自动驾驶项目”,百度Apollo计划也于不久后的2013年开始布局,全球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研究达到高潮,以至于到今天都是业界和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1925年的人们很难想到现在的技术方案,例如ADS雷达+摄像头的多传感器融合路线、FSD视觉解决方案等,而且无法规避技术风险,如有线感应技术的成本波动等。
从投资者和融资者的角度而言,往往需要通过投资才能够了解技术方案的潜力,该金融约束实质上增加了技术发展的多样性和可能性。然而极端不确定的投资挑战也会因创新过程的收益偏斜而变得更为复杂[3]。因此,对于项目的评估和创新投资的发展方向,需要借助专业的评估机构或技术中介的专业化服务。如知识产权机构Ocean Tomo在Nortel Networks EMEA债权人估值分配项目中,为各业务线一起出售的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作为第三方进行独立估值,评估分析专利预期收入,分析各债务人对应的发明和财务贡献,对其独家许可的相对价值进行评估,促成双方协商,最终实现的知识产权流动收益超过70亿美元[4]。
第二,发明投资理论的基础:知识产权财产权本质属性的理解。发明投资理论根基可追溯至知识产权的财产权本质。根据Blackstone的绝对财产权理论[5],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财产权同样具备排他、使用、处分、收益四大权能。然而,基于传统的民事法律框架的理解,应该将专利权的价值实现绑定于实施行为之上,毕竟要先“做蛋糕”,才能“分蛋糕”,这一观点也不无道理,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大量不具备实施条件或不适宜实施的主体的创新成果陷入空置的困境,空有专利而无法变现。NPE的出现实质上是民事法律中财产权理论的突破,通过剥离专利权的实施权与收益权,构建起权利持有到价值转化的桥梁,单独做一块技术价值转化的“蛋糕”。这一分离并非对专利权利完整性的破坏,而是将专利权的财产属性独立显化,不能与著作权与邻接权的类型进行简单类比。
在资本循环层面,传统风险投资依赖于企业股权的增值获取高额回报,其退出机制受限于技术商业化周期,也即传统风投要看准企业身价涨幅,简单类比就像投资性房地产,投资人的获利往往依赖房价上涨。具体而言,NPE从研发主体处收购专利时,一般会通过设立瑕疵担保条款与收益分成协议,将技术的不确定性内部化自身风险。瑕疵担保条款以合同形式保证专利权的法律有效性,降低NPE的后顾之忧,而收益分成协议则将许可费与专利实际使用情况动态绑定,减轻投资者评估具体技术前景的负担。
从交易成本理论审视,专利交易面临的交易成本包括搜寻匹配成本、议价签约成本、监督和执行的成本等等。在分散化的双边交易模式下,这些成本往往超过交易收益,导致市场失灵。NPE通过规模化的专利聚合与标准化的许可协议,将大量离散交易整合为系统化的权利流通网络,在技术交易中承担着中介的角色,一边为卖方提供搜寻客户,一边分析买方的实际需求,提供专业化服务,寻求卖家,促成交易。
第三,发明投资理论的总体含义:对发明投资指的是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的过程,它涵盖了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市场推广等创新链各个环节的资金筹集、分配和使用。创新活动要想持续发展,并进一步扩张,一定离不开有效的资金支持,而传统融资模式难以有效支持知识产权价值转化,这种矛盾更体现了发明投资理论的重要价值,即通过制度层面的设计与创新,将静态的知识产权转化为流动中的资本,重构创新价值链的资金循环机制。NPE作为这一模式的重要载体,既非单纯的专利聚合者,亦非舆论标签化的专利流氓,而是扮演着知识产权资本化进程中的中介角色,其存在本质上是法律对市场需求的回应,通过专业化运营填补创新成果的法律排他性与经济流动性之间的隔阂,从而得以实现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功能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平衡。
纵观发明投资理论的演进轨迹,NPE的法律角色呈现出鲜明的辩证特征,既是传统知识产权制度的挑战者,又是现代创新经济的建构者;既是资本逐利性的物质载体,又是技术扩散的法治化通道。在数字技术重构全球产业格局的当下,深入理解NPE在发明投资理论中的体现、回归NPE的本质特征,有利于超越“遏制”或“放纵”的简单政策选择,真正释放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赋能潜力。
二、NPE在知识产权流转环节中的作用
知识产权流转循环既体现出一定的线性流程,又体现出动态平衡的复杂性,通常表现为权利生成与确权、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知识产权交易、知识产权实施、争议解决、权利终止组成的链路。这套机制的核心在于让法律规则和市场力量形成合力,协同作用,将专利权转化为可流动的创新资本,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技术扩散、合理进行风险分配与提升价值的有机统一。NPE作为这个系统中链接各方的重要枢纽,既不像传统企业那样直接行使专利权利,也不只是单纯管理资本运作,而是通过法律关系的重构与交易结构的创新,在专利的诞生、确权、流通、实施等环节中承担起系统润滑与价值催化的功能,NPE在此期间搭建的便是排他性权利设定与流动性价值实现之间的桥梁。
知识产权流转体系的动态循环表现为权利生成与确权、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知识产权交易、知识产权实施、争议解决、权利终止组成的链路。NPE作为区别于传统产业实体的特殊权利主体,其运行逻辑渗透于每个流转节点,既推动着知识产权的市场化配置,也重构着法权关系的传统边界。
第一,NPE在权利生成与权利归属环节的作用:权属界定的中枢。自然权利理论将专利视为发明人智力劳动的自然延伸,而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讲,需要进一步强调专利制度的工具性价值。以大学和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机构为代表的NPE,通过预确权机制将专利申请时点前移至科研立项阶段,也即在立项和研发阶段就对可能的知识成果进行明确的约定,将权利生成前置化。在Stanford v. Roche案[6]中,斯坦福大学称Roche侵犯了其HIV检测试剂盒专利,这一案件源于斯坦福大学雇用的一名研究员,该研究员被他的导师安排在研究公司Cetus工作。该研究员首先与斯坦福大学签订协议,将他在斯坦福大学工作期间产生的“权利、所有权和利益”发明转让给斯坦福大学,随后又在Cetus签署了一份类似的协议。随后Roche收购了Cetus的PCR相关资产,并利用该技术商业化生产HIV检测试剂盒。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作出判决,认为研究员与Cetus的协议将其权利有效转让给了Cetus,之后随收购行为转移给Roche,并未否认Roche在该发明中的所有权权益。承包商们(contractors)通常自其员工和资助的机构获得任务,通过有效的任务,资助发明落地。联邦巡回法院最终依据《拜杜法案》确立的发明人优先原则,承认了NPE在职务发明权属界定中的枢纽作用。
第二,NPE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环节的作用:市场定价机制。一般而言,价值评估需要建立在实施的基础之上,出于思维惯性,市场倾向于预设专利价值只能或主要源于实施主体的生产实施活动。NPE的估值模型倾向于评估预期价值。NPE通过组建专利交易指数等金融工具,使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从个案判断转向市场定价机制。在Qimonda破产案件[7]中,涉案公司是一个涉及德国半导体公司,于2009年申请破产,其专利组合构成破产清算中的重要资产。该案件中,Qimonda的专利组合包括约12000项专利,其中至少4000项是美国专利。在NPE收购Qimonda专利组合的过程中,所进行的专利价值评估是确定交易价格的基础。NPE需要对专利的技术先进性、市场应用前景、法律稳定性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以确保以合理的价格收购专利,实现双方的利益平衡。同时,在公司破产、专利价值在破产程序中实现后,NPE还可以继续通过专利许可等方式继续盘活专利。
第三,NPE在知识产权交易环节的作用:将分散的专利加以聚合、形成面向全行业的许可方案。NPE通过收购、整合和再许可专利,使得原本可能被闲置或低估的专利重新进入市场,提升专利市场流动性。许多专利权人,如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小型创新企业,往往缺乏将专利技术商业化的专业能力和资源,甚至动机,导致大量专利无法有效转化为经济价值,极大地打击了高校及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进而严重阻碍了创新的步伐。除此之外,国内出于专利和知识产权成果对于职称认定、学位授予的关联评价,大量专利在获得授权的第二年就停缴年费,表面上确实能够固定高校斥巨资生成的知识成果,但本质上这些专利还是处于失效的状态,无法进行有效的市场应用和排他性对抗,这些专利从申请之初就没有被赋予“赚钱的期许”,科研人员评完职称,学生毕了业,这个专利就无所谓了,很难会有主体主动去维护此类知识产权。
而在这种情况下,NPE可以凭借其专业的知识产权运营团队和丰富的市场经验,能够精准发现潜在高价值专利,并通过合理的评估和交易,将其引入市场,促进技术的流动和扩散。针对小企业和个体发明人而言,NPE通过购买其专利或提供许可机会,使其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从而激励进一步的创新活动。NPE向小企业和个体发明人收购专利的行为,某种程度上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使得这些创新主体能够更加专注于技术研发和创新,而不必过于担忧专利的商业化问题[8]。对于高校和科研人员而言,NPE能够识别专利的价值,通过专利交易,得以进一步促成科研活动。国内有许多高校都制定了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在各大高校官网也能够快速查询到现金奖励、荣誉奖项的信息公示。高校科研人员或研究生,可能受限于工作和学习的性质不方便实施这些专利,但NPE可以借助其特性,推进交易进行,客观上可以有效提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专利池作为NPE中的一种形式,通过集合分散的专利资源、优化许可机制和平衡市场竞争,成为推动技术流转与产业协同。与传统产业实体的区别在于,专利池的运营者并不直接从事技术产品的生产制造,而是专注于专利资产的整合与交易。专利池管理机构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平台,将分散于不同权利人的标准必要专利进行聚合,形成面向全行业的许可方案,起到“超市”的作用,把各类货品集中到一个地方,方便顾客购买,这一特性对市场主体知识产权交易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第四,NPE在知识产权实施环节的作用:市场化的专利运营机制降低交易成本。传统实施权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权利,但NPE通过权利束分解创造出更加详尽的细分市场。NPE通常将其专利组合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许可,以简化许可流程和提高许可收入。同时,在技术实施层面,NPE通过市场化的专利运营机制显著提升了技术流转效率。大量由中小企业、独立发明人或科研机构持有的高质量专利,常因权利人缺乏商业化能力或谈判资源而处于休眠状态。NPE通过专业化运作收购此类专利并投入许可市场,实质上构建了技术供需之间的制度性桥梁。
第五,NPE在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环节的作用:系统性治理机制和预防性合规激励。如果深入剖析专利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争议解决机制的运行规律,可以得出,NPE活动客观上对争议的高效化解、法律规则的动态调适以及利益平衡的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源于专利权作为排他性财产权的法律属性,通过诉讼与谈判的相互作用,推动争议解决从零散对抗转变为系统化治理,最终服务于知识产权制度维护创新秩序的核心目标。同时,NPE的争议解决活动还提高了市场主体的风险预期,从而形成预防性合规激励。当企业意识到潜在侵权可能招致NPE的高成本诉讼时,便会主动建立起企业内部的专利风险防控体系,采取包括开展自由实施调查(FTO)、提前进行技术规避设计或寻求专利许可等措施。这种风险意识的觉醒,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自我调节机制,效果远超被动的事后救济。由此产生的威慑效应并非简单以诉促和,而是通过法律风险定价重新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提高企业未妥善技术布局的风险成本,使争议解决从个案对抗升维为系统性风险治理。
综上所述,NPE在知识产权全流程中的法律角色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并非简单介入某个具体环节,而是通过深度参与知识产权全流程运作,使其突破传统制度的阻力,将知识产权从对抗性权利转化为合作性资本,在排他性与流动性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法律通道。
三、交易安全与成本控制:NPE价值体现
知识产权的制度既要维护权利人的排他性利益以激励创新,又要促进技术成果的社会化流动。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迭代速度的加快使专利权的经济生命周期大幅缩短,而全球化竞争格局又要求创新要素的高效配置。NPE正是这种制度矛盾催生的适应性机制,其根本价值不必然在于是否直接参与技术实施,而在于通过专业化运作重构知识产权的价值实现路径。
一方面,保障知识产权流转的交易安全。在知识产权流转过程中,交易安全是维系市场信用的核心要素,本质上是法律对交易主体权益的确定性保障与风险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建构。NPE作为专业化的知识产权运营实体,通过市场化手段与法律规则的深度融合,在确权保障、风险分散、交易标准化等维度形成独特功能,使知识产权流转的安全性与效率得到大幅提升。这种作用的实现,一方面源于NPE依赖交易安全的稳定性进一步实现资产增值的需求,另一方面,NPE的专业化运营也可以反向推动交易规则的精细化发展,以交易数量和频次促进高质量发展,形成市场与法律的双向强化机制。
传统知识产权交易的个性化谈判模式虽尊重契约自由,但合同条款的任意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履约的不确定性,进而威胁交易安全。在交易结构设计上,NPE发展出分阶段支付、收益权证券化、反向许可等交易模式。比如,在专利证券化交易中,NPE可以将专利许可收益拆分为标准化金融产品,通过信托架构实现风险隔离,拓宽融资渠道,通过金融监管规则的外部约束增强交易透明度。在合同条款层面,NPE主导形成的许可协议范本可能进一步成为行业惯例,为业界提供更为专业的范本,如明确界定许可范围、设置自动终止条款、引入第三方争议解决机制等。NPE在保障知识产权流转交易安全中的积极作用,揭示了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中市场力量与法律规则深度结合的治理模式,通过专业化运营将法律文本中的抽象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交易规则,在确权、定价、交易等环节构建起多层次的安全保障网络。这一保障机制并非单纯依赖法律强制力,而是通过市场主体的经济交易过程中的理性而自发形成安全秩序,降低个体交易风险。在此过程中,NPE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市场参与者。这种治理模式的深层价值在于,知识产权交易安全的终极目标恰是市场力量与法律规则在相互作用中达致的制度均衡。
另一方面,降低知识产权流转的交易成本。在知识产权流转领域,高昂的交易成本始终是制约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障碍之一。这种成本不仅体现为显性的货币支出,更包含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检索分析、交易谈判、风险防控等隐性消耗。NPE通过专业化分工与市场化机制的深度介入,优化知识产权交易,进而系统化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NPE利用既有法律框架构建高效交易方式,另一方面,其商业实践又反向推动法律规则的适应性调整,形成成本优化的动态循环系统。
专利组合的构建和组合许可,可以在知识产权交易过程中形成比较优势,降低专利交易的成本。同时,NPE为专利持有者和企业家提供了退出机会,使其能够缩短研发再投入的周期,从而促进专业化研究进展。专利持有者或者企业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动机进行技术许可、技术商业转化等行为,NPE为此提供了额外的退出机会,可以使他们专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研发环节。[9]在技术供给侧,NPE对分散专利的集中收购实质上建立了技术资源仓库,买方可通过单一接口访问跨领域技术资产,搜寻成本较传统模式有所下降。在需求侧,NPE通过数据分析预判产业技术趋势,主动将沉睡专利与新兴市场需求对接,使技术流转从被动响应升级为主动引导。
综上所述,回望知识产权演进史,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都伴随着制度形态的深刻变革。NPE的兴起延续了这一历史逻辑,通过市场机制填补法律制度的适应性缺口,在维护交易安全与降低交易成本的方面发挥其独特的积极作用。这种价值实现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经济指标提升,也可从技术保护的防御性工具转变为创新驱动的生产性资本。专利非实施实体在我国的格局正从粗放式运营向专业化、合规化转型,法律风险与市场争议将通过制度完善、运营模式创新以及行业自律有所化解。未来,NPE若能深度融合产业需求,推动高价值专利转化,有望进一步成为中国创新生态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我们将在系列文章的下一篇深入分析NPE的运行模式,对NPE进行分类,论证这些类型的NPE是如何在推动创新、促进技术要素的转化和流通中发挥作用。
注释:
[1] See Yan Li, Yiren Zhang, Jian Hu, Zeyu Wang, Insight into the nexus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edge financing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with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Volume 93, Part A, 2024, Pages 700-719.
[2] Knight, F.H. (1921).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3] Scherer, F.M., & Harhoff, D. (2000). Technology policy for a world of skew-distributed outcomes. Research Policy, 29(4–5), 559-566.
[4] Ocean Tomo, Featured Engagement, https://oceantomo.com/featured-engagements/.
[5] 王铁雄:《布莱克斯通与美国财产法个人绝对财产权观》,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3-143页。
[6]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 v. Roche Molecular Systems, Inc., 563 U.S. 776 (2011).
[7] United States Bankruptcy Court, E.D. Virginia, Alexandria Division, In re QIMONDA AG, Debtor., No. 09–14766–RGM.
[8] 参见宁立志,龚涛:《专利非实施主体的价值评判与法律规制——以网络化开放创新范式为视角》,载《知识产权》2024年第4期,第92-108页。
[9] 魏洽,黄智明,毛昊:《NPE的创新影响:理论特征与发展实践》,载《科学与社会》 2024年第1期,第125-147页。
(原标题:NPE:从萌芽到当下的创新赋能之路)
来源: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
作者:张鹏 王搏琳 郑书发
编辑:IPRdaily辛夷 校对:IPRdaily纵横君
注:原文链接:NPE:从萌芽到当下的创新赋能之路(点击标题查看原文)

「关于IPRdaily」
IPRdaily是全球领先的知识产权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致力于连接全球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人才。汇聚了来自于中国、美国、欧洲、俄罗斯、以色列、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科技公司及成长型科技企业的管理者及科技研发或知识产权负责人,还有来自政府、律师及代理事务所、研发或服务机构的全球近100万用户(国内70余万+海外近30万),2019年全年全网页面浏览量已经突破过亿次传播。
(英文官网:iprdaily.com 中文官网:iprdaily.cn)
本文来自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并经IPRdaily.cn中文网编辑。转载此文章须经权利人同意,并附上出处与作者信息。文章不代表IPRdaily.cn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iprdaily.cn”

 共发表文章
1134篇
共发表文章
1134篇- 我也说两句
- 还可以输入140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