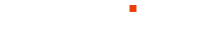#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未经作者许可,禁止转载,文章不代表IPRdaily立场#
来源: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
作者:王轩 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
原标题: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法律规制的思考
人工智能虽然并不是新概念,但其产物近来又掀起一波热潮:从AlphaGo战胜众多“世界级围棋手”衍生出的棋谱,到微软“小冰”作的诗,索尼计算机科学研究时的研究人员利用人工智能设备“创作”出的《Daddy’s Car》等。早期,人们研究机器产生的作品问题时,学者认为机器本身不具有人格因素,其不会产生具有“主动性”的创作。随着大数据的应用,计算机计算水平指数级的提升,当前的人工智能水平与过去相比显然不属于同一量级,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已经可以通过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做到自主学习,能够在多次训练后自主作出一些判断和思考,能够承担部分或者全部的创造性工作。[1]
日本2016年官方颁布的《知识财产推进计划2016》中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法律属性问题提上了日程。[2]根据该文本,在人工智能水平较高、机器人行业发展处于世界前列的国情下,日本当前的法律,并不认可机器自动生成的创作物时知识产权的客体。
一、“人工智能作品”的概念
根据熊琦的界定,对于人工智能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程式化内容生成自主行内容生成。前者是计算机程序和算法的预先设置而生成内容,后者则是居于使用者提供的素材自行分析生成的内容。[3]从技术发展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实现方式将分为使用符号性知识表达的人工智能系统和使用非符号性知识表达的人工智能系统。前者使用专业语言对知识进行编码,后者通过模拟人类神经系统来形成知识内容。[4]
有学者将人工智能根据“智能化”的程度划分为三个阶段:1.依托于智能硬件的“准智能阶段”,这一阶段并非真实意义上的人工智能阶段。2.依托于计算机润年的“算法智能”阶段,这一阶段授予人工智能收集数据、学习数据的方法,但此阶段的人工智能并未脱离编程者的算法构架儿具备独立创作算法的能力。3.全脑仿真阶段,即所谓的“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模仿人类的生物神经系统的人工智能的方法。
在研究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是否构成作品时,需要首先考虑一下与之相同表现形式的作品如果出自人类的创作能否构成作品,这样逻辑上更清晰,避免了一些无意义的讨论。对于那些符合这一条件的内容,王迁认为应当是应用算法、规则和模块的结果。他进而认为算法、模块和模版是否为智力成果,与应用算法、规则和模版的过程是否属于智力创作,产生的结果能否构成作品并无必然联系。[5]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既应当首先界定探讨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意义上的属性时的范围,使得讨论的框架基于实践理性之下。
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法律属性
规定人工智能创作物版权问题的国家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国际组织层面对于这一问题上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实际上各国面对这一问题目前尚未有比较突破性、激进的立法,一方面与各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尚未达到“成熟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各国对于著作权法的慎重考虑密切相关。
(一)各国立法例
目前的世界各国中,大部分国家尚且没有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版权问题进行详细地讨论,已经认识到、且试图从法律和政策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的国家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主。
英国明确地对部分计算机创作物进行了规定,其给予计算机创作物以人类作品完全同等的地位。英国法将人工智能生成物定义为:在不存在任何人类作者的状况下,由计算机运作生成的作品。对于该类作品,英国法规定其版权人是对该作品之创作进行必要安排准备工作者。对于此类作品,英国法规定其保护期限是该作品生成之年份起算50年末;著作人格权不适用于该作品。上述规定主要体现在英国1988年《版权、设计与专利法》第9条第3款、第12条第3款、第79条第2款C项、第81条第2款、第178条规定了计算机生成作品(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处理。
以英国、南非、新西兰为代表的部分英联邦国家认可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并将这一类型作品的作者视为人工智能的操作者;澳大利亚虽然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但在政策上一定程度地认可了部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而且,英美法系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知标准,英国、南非等国家已经基本上接受了纯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而澳大利亚针对版权作品的创作主体的资格认定标准则明显更为严格,其对人工智能操作者的要求不仅仅局限于普通的操作行为,还要求其对创作作品的物质形式具有一定控制力,纯粹的人工智能创作物在澳大利亚法中无法取得版权。
美国虽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讨,并认为这种类型的作品一般只要符合《版权法》的标准即可以被授予版权,但司法实践上针对人工智能创作之作品的认定、权利归属尚缺乏一致的做法,编程者和操作者目前都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的版权人。1993年以前,至少有两份经由计算机软件创作的文字作品被美国版权局登记在册,并授予版权,美国版权局虽然将编程者视为版权人,却将计算机软件列为作者。由此机器的地位相当于为实际操作者“打工”的行为,与职务作品或者说法人作品的逻辑有相似之处。
除日本之外,大陆法系国家中则几乎没有国家在法律和政策上尝试回应人工智能创作物的问题。日本政府设立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在一份报告中 指出“一般认为,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不属于著作权的客体”,其原因就在于“人工智能自动产生的创作物(类似作品的信息),并非(日本)《著作权法》第2条第1项规定的‘表现思想或者情感的作品’,也就根本不存在对其享有的著作权”。
以WIPO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并不试图以公约的形式对人工智能创作物所引发的版权问题进行统一规定。从1982年的建议和1991年的最初讨论内容来看, WIPO本身对于计算机创作物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处在变化之中,已经显然不再将计算机视为一种协助创作的技术手段,而开始考虑将其作为创作的“主体”。从1991年WIPO最终撤回关于计算机创作物版权问题的讨论这一动向来看,至少目前,国际组织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版权问题交由各国国内法予以处理,选择了不介入的态度。[6]
(二)国内权威学者观点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权威解释,作品须具有独创性,应该是作者自己创作的,完全不是或基本上不是从另一作品抄袭来的。我国学者吴汉东认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解释,对于人工智能内容,只要是有机器人独立完成,即构成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至于其用途、价值和社会评价则在所不闻。他认为可参照著作权法关于职务作品和雇佣作品的规定,由创设机器的“人”而不是机器人去享有和行使权利。[7]
然而王迁主张,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2条将享有著作权的主体限定为“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无国籍人”,体现了著作权法保护的主体是人,在主体问题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不构成作品,属于法律对其的应然定性。然而,当人工智能生成物与人类创作的作品类似时,若实际操控者未披露生成的过程,而且还在作品上署名,则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以署名推定的规定,此中情况下实际由操控者取代了“机器”称为创作者,这种情况应属特殊情况。王迁认为这种情况本质上属于证据规则的范畴,在未有人工智能出现前也仍然存在此种情形,比如“猕猴自拍”。[8]也就是说此种情况下,如果证据不能推翻,则其构成实然法意义上的作品。
不过,王迁的观点是在首先确认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应当依照实然法的态度下进行的,也就是完全按照现行法律的思路下展开的,对于人工智能内容的划分也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具有实践理性——人工智能设备在未来深入学习后,创作的作品可能完全无法区分,但设备是不会累的,并且生产效率极高。如果将无法区分是人创作还是机器完成的作品,仅按照证据思路,根据署名判定,虽然可行,但是否会冲击人类的创作价值?毕竟物以稀为贵。同时上述的思路还存在一个问题,便是人工智能开发者如果无法主张人工智能机器人是作者,为了证明作品来自人工智能设备,又不以上述所言自己是作者主张权利,即使作品符合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也依然会产生“孤儿作品”的问题,而为了证明人工智能的成果这种问题一定不会是少数现象。这种情况所带来的困境是;一方面无法规制对此类“作品”的抄袭问题,毕竟“无权“何来侵权;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得到正向经济反馈,也不利于人工智能的良性发展。
在独创性方面,王迁也持与吴汉东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当下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容是执行既定流程和方法的结果,是应用“人”的“智能”,其生成内容的过程并不涉及创作所需的“智能”。[9]吴汉东则认为,独创性的判断标准值得商榷,“艺术价值不高的作品,与艺术性高的作品一样能产生著作权。”[10]不过,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生成成本十分之低,如果不区分创作性,则会产生一系列水平较差的“作品”,这种低水平的“创作”泛滥,也必然不会是法律规制所欲达到的目的。
关于人的因素,也有学者从法理学的角度入手,论述:虽然概念法学僵化,利益法学风靡,但是学者们仍然会借助概念法学的分析方法来限制利益法学的恣意。当前这种急于给人工智能内容确立法律地位的思想按照该学者的思想属于利益法学的观点。如果社会生活是第一性的,那么法就是第二性的,法是根据人的需求构建的,要求自身不能忽略社会生活。修辞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这种主观性不能以牺牲生活事实的客观性为代价。法的第二性远离在操作层面上就是一个选择、评价与取舍的过程,在法律术语运用上反映需要法律关注的部分事实,舍弃非要件事实。需要进一步澄清的事,虽然法律逻辑、法律解释与法律修辞构成了法律基本方法,在解决具体问题上也是相互辅助的关系,但是按照法的第二性原理进行评价与取舍病不能直观的在法律方法上得到回应。萨维尼将此看做是一行带有创作性的法律活动。进而该学者得出结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产生在版权法意义上讲,具备了可以视为代表人工只能所有者意志的创作行为的基础。此处采用“视为”的拟制方法是有正当性的:从价值评判标准和人格因素的来源角度来看,视为没有超出生活事实的客观性;其二,符合限行版权法关于法人和其他组织视为作者的拟制规范,人工智能自身产权界定上归于出资者,人工只能的创作也代表了出资者的意志,这隐含了一旦因人工智能创作物引发侵权,自然应有人工智能所有者承担。[11]
三、对人工智能作品规制的设想
立法的滞后性常被人们诟病,常见的批评如:目前我国尚无相关法律对这一问题进行规制。但是,法律的严肃性、影响的全局性也必然决定了其必须相对稳定,不能因为社会一点尚未明晰的动向就迅疾修改抑或造新法。虽然根据上述分析,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已经开始能够构成对现行法律规制的一些挑战,但当前的情况依然可以以政策引导、鼓励。因人工智能,大修《著作权法》目前看来并不可行。启动相关立法恐怕还要等人工智能的体量、智能程度远超目前时,至于程度,可能应当是因人工智能产生的内容对社会造成一定量级的影响时。虽然不能量化那个时刻的状态,但至少应当不是人工智能内容还是很新奇的物品。
也有学者从激励论和市场的角度分析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法律意义,其认为不授予人工智能创作物以版权最明显的优势在于避免了法律修正的成本,传统的版权体系得到了形式上的维护。劣势在于《著作权法》将无法回应人工智能技术造成的冲击。对于上述问题,该学者提出的思路包括重新思考人工智能作品的归属、版权保护期限及权利内容,也就是说把“人工智能作品”和“人类作品”在立法时应当区分对待;其次法律应当能够保持人类作品与人工智能作品在市场上既竞争又共存。[12]这些讨论可以称为上文所述合适时机来临时修法、立法的一些有益思路。
参考文献
[1]王文亮, 王连合. 将法律作为修辞视野下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考察[J]. 科技与法律, 2017(2):60-66.
[2][4][6][12]曹源.人工智能创作物获得版权保护的合理性[J]. 科技与法律, 2016(3):488-508.
[3]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J]. 知识产权, 2017(3):3-8.
[7][9]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17, 35(5):148-155.
[8]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7, 35(5):128-136.
[10]吴汉东.知识产权法 [M].4 版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4.
[11]王文亮,王连合.将法律作为修辞视野下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考察[J]. 科技与法律, 2017(2):60-66.
来源: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
作者:王轩 厦门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院
编辑:IPRdaily赵珍 校对:IPRdaily纵横君
推荐阅读
“投稿”请投邮箱“iprdaily@163.com”

「关于IPRdaily」
IPRdaily成立于2014年,是全球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媒体+产业服务平台,致力于连接全球知识产权人,用户汇聚了中国、美国、德国、俄罗斯、以色列、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科技公司、成长型科技企业IP高管、研发人员、法务、政府机构、律所、事务所、科研院校等全球近50多万产业用户(国内25万+海外30万);同时拥有近百万条高质量的技术资源+专利资源,通过媒体构建全球知识产权资产信息第一入口。2016年获启赋资本领投和天使汇跟投的Pre-A轮融资。
(英文官网:iprdaily.com 中文官网:iprdaily.cn)

本文来自IPRdaily.cn 中文网并经IPRdaily.cn中文网编辑。转载此文章须经权利人同意,并附上出处与作者信息。文章不代表IPRdaily.cn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iprdaily.cn/”

 共发表文章
31245篇
共发表文章
31245篇- 我也说两句
- 还可以输入140个字